当 OpenAI 前首席科学家伊利亚・苏茨克维创立的 AI 机构 SSI 宣布联合创始人丹尼尔・格罗斯离职时,行业的目光再次聚焦于 Meta—— 这位 AI 新贵的 “叛将” 转身加入扎克伯格麾下,成为 Meta AI 产品部门负责人。这场看似普通的人事变动,实则是 AI 时代人才争夺战的缩影,更撕开了扎克伯格与 Meta 在技术竞赛中日益加剧的焦虑面纱。

一、从 “挖角” 到 “收购”:扎克伯格的激进人才策略
格罗斯的离职并非孤例。Meta 近期掀起的 “数百亿美元 AI 招聘潮” 早已引发行业震动:向 Scale AI 投资 140 亿美元以吸引创始人汪韬及核心团队,挖走 OpenAI 超级对齐团队前成员,甚至被曝为挖角开出 1 亿美元签约奖金(尽管新聘研究员公开否认)。这种 “暴力抢人” 的姿态,与 Meta 内部的人才流失形成刺眼对比 ——Llama 研究论文 14 名原始作者中 11 人离职,直接导致 Llama 4 Behemoth 模型因基准测试表现不佳推迟发布,工程师陷入 “恐慌模式”。
苏茨克维在回应 Meta 收购 SSI 的传闻时直言:“我们专注于构建安全的超智能技术。” 但扎克伯格显然等不及。对 SSI 领导层的挖角,本质是对 OpenAI 技术基因的 “精准狙击”—— 苏茨克维作为 ChatGPT 背后的 “扩展定律” 倡导者,其创立的 SSI 已获 Alphabet、英伟达投资,估值 320 亿美元,成为 Meta 眼中最具威胁的潜在对手。
二、焦虑根源:Meta 在 AI 赛道的 “内忧外患”
扎克伯格的激进策略,实则源于 Meta 在 AI 领域的双重困境。
- 技术短板与路线危机:Llama 系列模型虽一度被视为 OpenAI 竞品,但核心人才流失使其技术迭代受阻。当 OpenAI 凭借 ChatGPT 引领生成式 AI 浪潮时,Meta 仍在为模型性能与落地场景挣扎,甚至被曝 “管理层担心无法证明 AI 投资的合理性”。
- 行业竞争的碾压式压力:OpenAI 估值超 2000 亿美元,Anthropic、Inflection 等新贵接连崛起,而 Meta 在社交领域的基本盘正面临 AI 时代用户注意力迁移的挑战。山姆・奥特曼曾直言:“Meta 将我们视为最大竞争对手,但其 AI 进展未达预期。” 这种差距迫使扎克伯格用 “钞能力” 缩短时间差。
三、人才战背后:AI 行业的资本与技术博弈
这场人才争夺战早已超越企业竞争范畴,成为 AI 行业发展逻辑的缩影。
- 资本对技术话语权的争夺:Meta 对 Scale AI 的投资、SSI 的 320 亿美元估值,印证了顶尖人才与技术团队已成为资本追逐的核心资产。正如苏茨克维所言:“我们拥有计算资源和优秀团队,知道该怎么做。” 这种底气背后,是资本对技术路线的背书。
- 技术伦理与商业目标的冲突:SSI 以 “安全超级智能” 为使命,而 Meta 的挖角更侧重产品落地与市场竞争。当苏茨克维吐槽 “数据极限” 时,扎克伯格正用资本加速人才流动,试图在 “模型规模扩展” 与 “数据质量困境” 中杀出一条血路。
四、结局未定:激进策略能否扭转 Meta 的颓势?
尽管扎克伯格集结了格罗斯、汪韬等顶尖人才,但 Meta 的焦虑仍未解除。Blind 平台上匿名工程师的反馈揭示深层矛盾:“巨额投资的合理性” 始终悬在头顶。技术突破需要时间积淀,而挖角带来的短期人才堆砌,能否弥补底层研究的断层?当 Llama 4 的发布日期一推再推,当 OpenAI 紧急调整薪酬策略应对挖角,这场豪赌的胜率依然成谜。
AI 时代的竞争,终究是技术生态与人才体系的长期较量。扎克伯格的焦虑,或许正是行业洗牌的前奏 —— 当资本、人才、技术在方寸之间激烈碰撞,谁能在这场 “零和博弈” 中笑到最后,仍是 AI 史上最悬念迭起的章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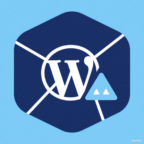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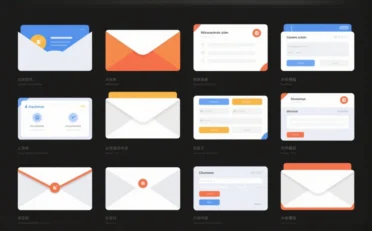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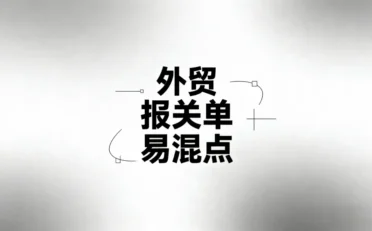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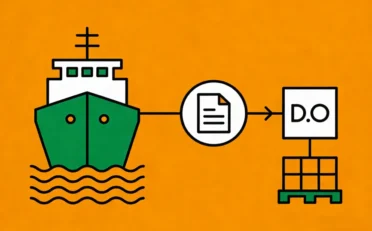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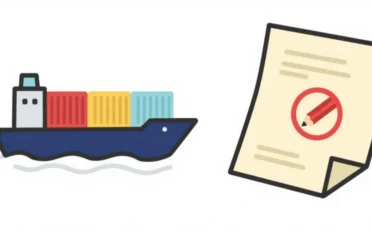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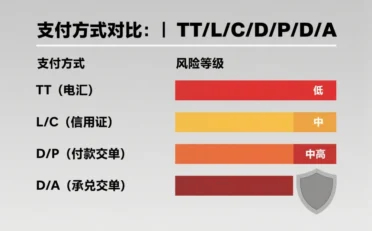
😂 那老哥,元宇宙花了那么多钱,最终不还是不提这茬了,现在再跟不上AI的潮流,就会沦为时代的弃子